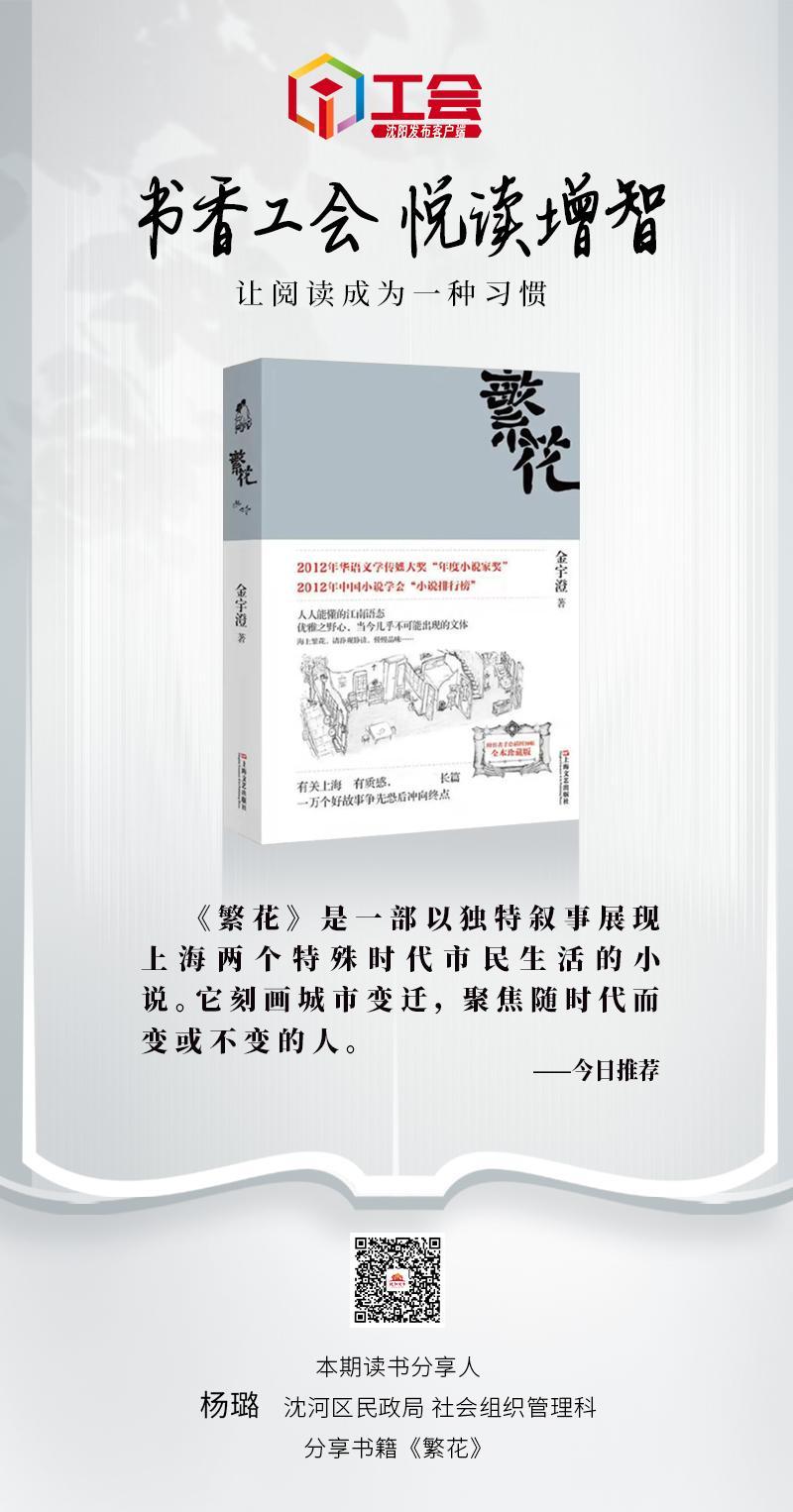
今天由我向大家分享《繁花》这本书。
第一次知道《繁花》还是几年前,之后是在杂志上看到对金宇澄的采访。
小说的叙事和曾看过的方式不太一样,人物间的对话没有双引号,像一个小酒馆里的说书先生,慢慢地、细细的,还稍微带点悬念地讲给你听。
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评论《繁花》,是“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和最好的城市小说之一。小说中所记叙的时代起于20世纪60年代,终于90年代,着重刻画了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上海市民在时代洪流下的“随波逐流”,以及深刻与点滴不曾改变的上海生活。表达内容在沪生和阿宝年少与年长之前来回穿梭,各种人物登场,旧人一去,新人顶上。
—————————
时间不会中断
如潮水般涌过去
忽大忽小
忽左忽右
—————————
小说的章节布局采用两条主线并行的样式,单章描述的是主人公幼年的经历,双章描述的是主人公长大后的故事。两条线并行,亦交织。
顺时间而读,收获的是主人公成长的欣喜,交互而读,就更多了几分惊喜在其中,难免连连惊叹。
刻画一座城市的变迁,最直观的不是去记录这座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楼,亦不是那轰然倒塌的铁塔,而是去观察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
无论时代如何的发展变化,城市如何变迁,这座城市永恒的恰是那些随着时代而变,或不变的人儿。
目录后第一页,一句“上帝不响,一切全由我定……”,颇有韵味。这句话看到后半段的时候,从春香口中再说一遍,才真真是击到我。
再读下去,从将要与这个世界告别的阿毛口中说出,是与亡妻的旧言相契了。故事到这里,一下子让之前所有纷繁复杂的故事都沉淀下来,弄堂里三种不同家庭背景的小市民的生活的底色翻涌出来又归于沉寂。
故事里出场了很多人物,有时候一度分不清到底是谁经历着什么,但不用着急在前文漫天翻找,慢慢跟着他们经历下去,饮食男女,从小囡到中年,一个个都从地道的上海话为背景的弄堂里走出来。
也是苏州的沧浪亭旁熬出黎明,也在理发店的楼上过生活,也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也在破败不堪的乡下小房辗转难眠。这里面,有男女婚姻爱恋暧昧之事,有兄弟互诉寄托彼此帮扶之事,有市井人的闲言碎语,有小人物的冷暖自知。
我读书,习惯摘记,只是这篇五百五十页的“话本”,容我写下的句子少之又少。这故事都融在一张一合的对话里,都融在一颦一笑、一来一往中。金宇澄先生的文字不似张爱玲,不是女性的那种有点优雅和温婉的文字。
以前阅读张爱玲的文字,那种文字的气质可以渲染到自己的文笔里,落笔都是那种温柔的味道。但是金宇澄先生的文字,用着地道的上海话,带着上海人的气场,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另一种男性的上海味。
更妙的是,这文字带着上海的味道,更带着上海历史的味道,从最底层的贫苦到最令人羡艳的富足,从革命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人物的话语都契合着他的出身,他的立场,他的性格。
所以当我慢慢翻动纸页,从单双章节的两个时间线下慢慢走进这些人的时候,我不是唐突闯入的局外人,不是躲在暗处的偷窥者,我可能是一个经过的行人,也可能是一起生活在弄堂里的居客。
我记得看杂志的时候采访金宇澄先生如何处理书中的那么多人物,金先生回答时恰说道为什么将这本书题名为“繁花”。他说,“繁花”真好,常见字,符合小说里那么多人,星星点点的特点。
我想这就是每个小人物的存在,他们是星星点点的花儿,簇拥在一起,绽放出上海的春天。
我记性不好,但隐约记得故事里的人也有自嘲,说自己是灰尘。其实不论是灰尘也好,花朵也好,我们都是某段历史中某个角落里的小市民,也许无足轻重,无关痛痒,但谁又能说,这段历史选择了我,不是我的幸运。
无论是在上海的弄堂,还是在沈阳的小城,每一处、每一天都有故事在上演。
我看这些用文字、用镜头描述的故事,为之动容,才明白不同的花朵,会经历一样的风雨。“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
世上这么多人,人间这么多事。我占着小小一隅,也不知故事会如何进行。但总归,这生活全由我定。

来源:沈阳发布客户端“i工会”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