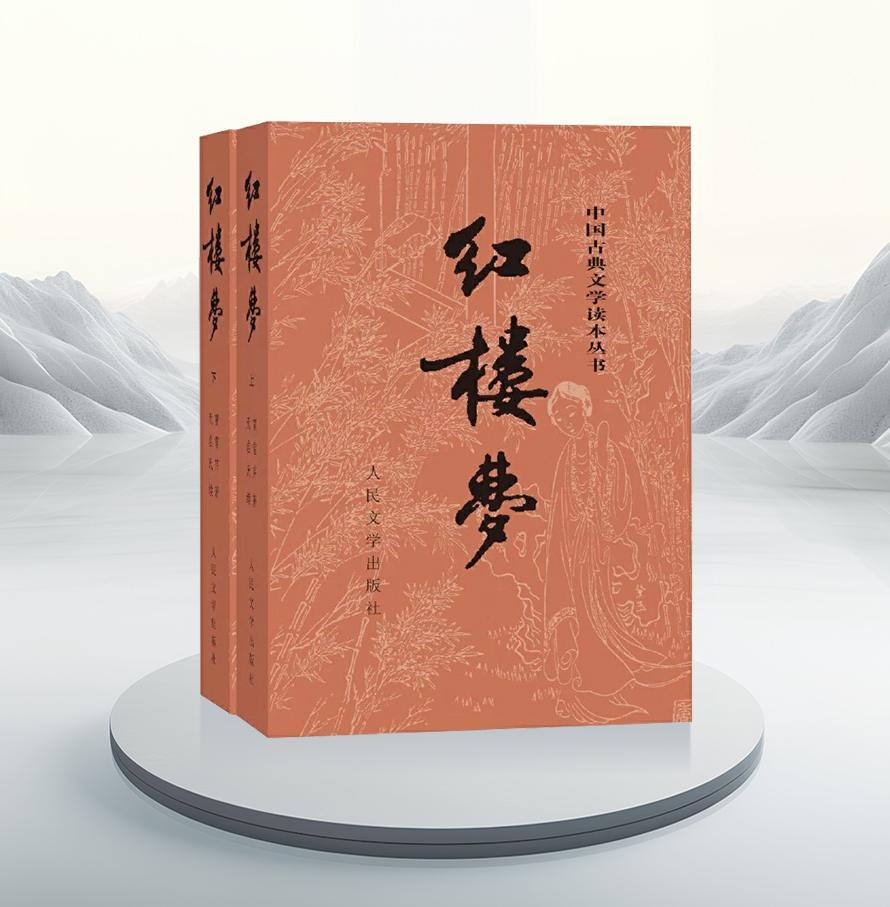书香工会 悦读增智
今天i工会邀请
天光社区
葛群芳
向大家介绍
▼▽▼
《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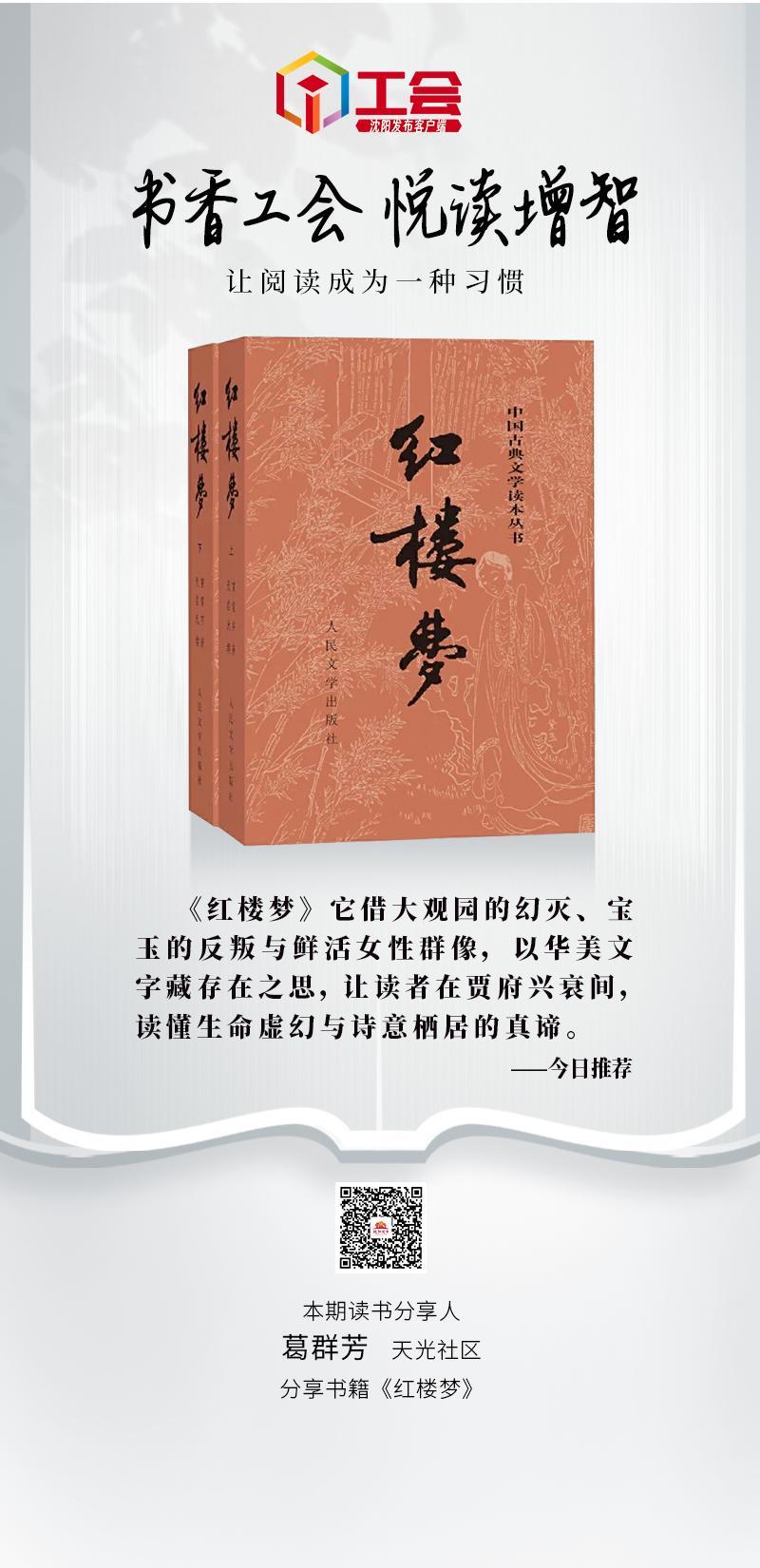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的这首自题诗,道出了这部千古奇书的本质——它既是一场华美至极的文学盛宴,又是一曲深沉的存在悲歌。当我们穿越那些精雕细琢的诗词歌赋、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家族兴衰,最终触摸到的,是人类面对存在本身时那种永恒的困惑与痛楚。
大观园是曹雪芹精心构建的一个乌托邦式存在空间,在这里,青春、诗意与美似乎可以暂时摆脱世俗的束缚而自由绽放。宝玉与姐妹们结社吟诗、赏花斗草的生活,构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封闭世界。然而,这种完美恰恰是虚幻的。
贾宝玉这一形象,是曹雪芹对传统价值体系最为激烈的反叛。他厌恶功名利禄,逃避成人世界的责任,沉溺于女儿国的温柔乡中。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生活方式,实则包含着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执着追寻。宝玉的“痴”,是对世俗价值体系的彻底否定;他的“顽劣”,是对规范化生存的坚决抵抗。宝玉最终选择出家,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对存在真相的终极领悟——他看透了所有世俗价值与情感依附的虚幻本质,选择了最为彻底的疏离姿态。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极端追问,使宝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复杂也最为现代的人物形象之一。
《红楼梦》中的女性群像构成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生命诗学体系。林黛玉的敏感多愁、薛宝钗的圆融世故、王熙凤的精明强干、史湘云的豪爽天真……这些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共同演绎了生命可能呈现的多样形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赋予这些女性角色以超越时代的自主性与复杂性,她们不是男性视角下的简单符号,而是具有完整人格的独立存在。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等经典场景,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最为动人的生命诗篇。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曹雪芹不仅颠覆了传统文学中的性别叙事,更展示了生命在种种束缚中依然能够绽放的绚烂姿态。
《红楼梦》对时间与记忆的处理极具现代性。小说开篇即通过"石头记"的神话框架,将故事置于一个超时间的维度中审视。这种叙事策略暗示了:所有的兴衰荣辱,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唯有通过艺术的转化,瞬间才能成为永恒。曹雪芹通过"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辩证思维,消解了现实与虚幻的绝对界限。大观园的美好时光,因为注定逝去而在记忆中显得更加珍贵;而记忆本身,又因为其不可靠性而成为一种创造性的重构。这种对时间与记忆的复杂思考,使《红楼梦》具有了现象学意义上的深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见证了贾府的兴衰,更体验了时间本身的流动与凝固。
《红楼梦》最终告诉我们:生命如一场幻梦,但正因其虚幻,才更显珍贵;存在本质是痛,但正因其痛苦,才更需要诗意地栖居。在幻灭与永恒之间,曹雪芹选择了用文字抵抗时间的侵蚀,用艺术超越存在的局限。